
在审理合同纠纷案件中,确认违约方的赔偿责任应当遵循“可预见性原则”,即违约方仅就其违约行为给对方造成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对由于市场风险等因素造成的、双方当事人均不能预见的损失,因非违约方过错所致,与违约行为之间亦没有因果关系,违约方对此不承担赔偿责任。

2004 年1 月2 日,亚坤公司与康瑞公司签订棉花购销合同,约定康瑞公司向亚坤公司提供229 级(二级)皮棉1370 吨,单价每吨16900 元,皮棉质量按国家棉花质量标准GB1103 - 1999 执行,康瑞公司对质量、重量负责到底,质量、重量出现重大问题,以公证检验为准。后经鉴定显示:康瑞公司向亚坤公司所供皮棉总计:二级皮棉1. 618 吨;三级皮棉523 . 416 吨;四级皮棉564 . 525 吨;五级皮棉21.643吨,合计重量为1111 . 202 吨,销售货款合计12733990 . 29 元,亚坤公司货款本金损失为6659358.11元。《2004 年棉花市场回顾及2005 年市场展望》一文载明:由于2003 年棉花减产,国内棉花销售价格一度冲至1 .75 万元/吨的水平。价格如此飙升,既有产需缺口扩大的因素的影响,也有“买涨不买跌”的恐慌心理在起作用。而在国家分两次共增发150万吨配额和紧缩银根等宏观调控政策引导下,国内棉花价格出现了回落,棉花销售价格在6月下降到了1. 5 万元/吨,随后受2004 年棉花大丰收心理预期影响,国内棉花销售价格已经下降到了1 . 13 万元/吨,比年初下降了35%。最高人民法院二审认为:本案合同签订的2004年1月,恰逢国内棉花市场价格飞涨,但到了2004 年5、6 月以后,棉花市场价格回落,此期间每吨相差5000 ~ 6000 元。亚坤公司在2004 年6 月以后转售的棉花,即使质量等级不变,也必然会出现因市场行情所致的收益损失。原审判决认定的亚坤公司本金损失6 659 358 . 11元不仅包括了棉花减等的差价损失,亦包括在此期间因市场行情下跌所造成的收益损失。该部分收益损失显属市场风险造成的,非为双方当事人所能预见,亦非康瑞公司过错所致。因康瑞公司与该部分损失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故康瑞公司不应承担市场行情变化导致的亚坤公司的收益损失。原审判决将亚坤公司在市场行情低迷时基于转售关系所形成的销售价格与本案行情高涨时形成的购买价格之差作为亚坤公司的损失由双方分担显属不当,不仅合同关系各不相同,亦有违公平原则及过错责任原则,二审法院予以纠正。亚坤公司关于康瑞公司应补偿其棉花收益损失6152 857 . 22 元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二审法院对亚坤公司在购买棉花时所发生的实际损失,即棉花重量亏吨损失及质量减等的差价损失予以确认,对于其他损失部分,即市场风险所致的收益损失、转售期间发生的运输费用、与案外人发生的借贷利息损失,均因缺乏合同依据及法律依据而不予支持。在处理违约责任时,《民法典》第五百八十四条确立了可预见性规则的核心原则:违约方需赔偿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这一规定是对1999年《合同法》第113条的修订与完善,旨在确保赔偿公正合理,并避免重复适用惩罚性赔偿规范。该条款明确“合同义务”涵盖给付、附随、解除后的恢复原状或补救措施等,但不包括先合同义务和不真正义务。其核心在于违约方在订立合同时应预见可能造成的损失范围,以确定赔偿额度。“造成的损失”指的是违约行为导致的财产减损,既包括直接损失也涵盖间接的可得利益损失。可得利益是指未来预期获得的利益,而非履行合同本身所获益的部分。它必须具有一定的确定性,即在违约发生时并未实际享有,但通过合同履行可以实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进一步细化了这一概念,强调可得利益作为未来利益,在违约时未被实际占有或享受,其存在依赖于合同的正常履行。同时,它要求损失具有确定性,以确保赔偿请求的合理性和可行性。综上所述,《民法典》第五百八十四条通过明确可预见性规则和损失范围,旨在平衡双方权益、促进市场公平与效率。这一规定不仅为违约责任的判定提供了清晰指引,也体现了对合同预期利益保护的重视,对于维护交易安全、促进经济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在生产利润损失的法律纠纷中,特别是在设备和原材料买卖合同中,双方因逾期交货或受领物品延迟而产生的经济损失尤为突出。买方可能面临生产延误导致的利润损失,而卖方则可能因为无法及时收回货款并承担额外保管费用而遭受损失。以华锐公司诉新龙公司的案例为例,新龙公司向华锐公司购买多组发电机后,因市场价格大幅下降(20%),远超正常行情下的5%,双方未能就价格重新协商达成一致。新龙单方面解除合同,导致华锐公司已生产的部分发电机组面临转售风险。一审法院考虑到华锐公司生产进度已达三分之一,判决新龙承担转售这部分货物差价损失的赔偿责任。然而,华锐公司对此判决不服并提起上诉。二审法院认为,市场价格波动不应成为违约方预见损失的依据,但交易惯例显示当价格变动超过5%时通常会重新协商供货价格,这表明买方对5%以内的价格变动具备预见能力。因此,20%的价格下跌超出了合理预见范围。综上所述,在处理生产利润损失纠纷时,不能仅将生产利润差额作为违约赔偿的唯一标准。应综合考虑具体案情、市场价格波动幅度以及行业惯例等因素,判断违约方是否能合理预见并承担相应的经济损失。当价格变动超出正常市场预期和行业惯例时,违约方可能需要对超出部分造成的损失进行赔偿。经营利润损失在承包、租赁和提供服务等合同中较为常见,特别是在违约方的行为导致守约方无法实现预期收益时。此类损失的赔偿通常基于已履行期间的利润率进行估算。以刘某兵诉三益公司合同纠纷案为例,双方签订三年种猪代养协议,约定由刘某兵负责饲养并承担相应费用,同时接受公司的指导和疫苗提供服务。然而,在第三年,刘某兵单方面终止合作,并自行处理疫苗和服务事宜,导致三益公司遭受经济损失。一审法院综合考虑了前两年的合作情况、家畜行业市场风险以及赔偿不应超出合理预见范围等因素,判决刘某兵赔偿三益公司10万元损失。对此判决,刘某兵提出上诉,但二审法院认为,作为多年从事牲畜养殖的从业者,刘某兵应当预见到其违约行为可能给三益公司带来的经济损失,并据此驳回了上诉。《民法典》中关于“可能造成的损失”的规定,强调的是在合同违约时,赔偿金额应基于合理预见范围内的预期损害。因此,在裁量未违约方的可得利益损失时,法官需综合考虑合同履行情况、行业特性、市场风险以及违约方对潜在损失的预见能力等多方面因素。在处理转售利润损失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前形势下审理民商事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第9条明确指出,在涉及先后系列买卖合同的情形中,原合同出卖方违约导致其后转售合同出售方可能遭受的可得利益损失通常被视为转售利润损失。然而,实践中一些法院直接以守约方向第三方签订的合同价款与原合同价款之间的差额作为赔偿金额,这种做法过于简单化且缺乏全面考虑。以西藏杰集金属矿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藏杰集公司”)与青海景丰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青海景丰公司”)买卖合同纠纷案为例。双方签订的《工矿产品购销合同》约定在特定期间内,青海景丰公司需向西藏杰集公司供应锌精矿,但实际履行中未能按约足量供货。在此背景下,西藏杰集公司与上海红鹭公司签订了《锌精矿买卖合同》,但由于青海景丰公司的违约行为,导致无法向上海红鹭公司提供足够货物,从而主张损失2511695.84元。一审法院认为该损失缺乏证据支持和合同依据而不予认可。二审法院则强调了赔偿原则应以补偿性为主,并考虑可预见性规则的约束。其分析指出,西藏杰集公司提交的《锌精矿买卖合同》并未实际履行;未能证明违约是导致未履行合同的原因;且无法提供证据证明因青海景丰公司的违约行为造成的具体损失。然而,在讨论此类问题时,我们应认识到,直接将转售合同差价作为赔偿金额的做法可能过于武断。在确定赔偿金额时,应当考虑转售合同是否实际执行、未执行与违约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以及合同双方的告知义务等因素。合同是基于双方真实意愿签订的法律文件,在特定情况下发生影响责任大小的突发情况时,守约方应履行相应的通知义务。如果在合同签订或履行前,守约方已与第三方签订了转卖合同,那么不能简单地要求违约方承担全部赔偿责任,这不仅可能对违约方不公平,还可能抑制参与交易的积极性。在处理可得利益损失时,法院需综合考量合同条款、双方行为及市场因素,确保赔偿公正合理。以杜某博诉孙某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案为例,尽管孙某违约导致房价上涨,但其无法预见政府拆迁对房价的影响,故仅承担双倍返还定金的责任。然而,若卖方在房价上涨后拒绝履行或转售获利,其收益应视为可得利益损失的参照物。司法实践中,法院对于未约定且难以预见的可得利益损失持保守态度,这增加了守约方的举证难度。如贵州妍绮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惠水县自然资源局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纠纷案中,尽管妍绮公司因土地被收回遭受了经济损失,但未来房地产市场波动性及预期收益不确定性导致法院未支持其关于预期收益的赔偿请求。对此,应明确可得利益损失的范围不仅限于书面约定,只要违约方在签订合同时可以预见潜在损失,无论是否通过合同条款明确,均应在赔偿范围内。司法实践中,法官不应仅以损失难以预见为由驳回守约方的诉求,而应更全面地考虑合同目的、市场预期及双方行为对可得利益的影响。

《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CISG)提供了具体规则,可以作为参考。在判断是否“可预见”时,法律通常以违约方能否预见到损失为标准。然而,这一标准引发争议,部分学者主张采用双层标准——即考虑违约方和守约方的视角,或引入理性第三人的观点来确保公平性。CISG采纳了双重标准:不仅要求违约人自身能预见风险,还要求一个同等资格、通情达理的人在相同情况下也能预见。这一规定增加了可预见性的客观性,但同时也带来了举证责任与归责原则的复杂性。关于判断时间,学界存在不同观点。一种主张以合同订立时为基准,认为合同履行过程中的风险不应由违约方承担;另一种则强调在合同履行前的所有可预见风险都应纳入赔偿范围。CISG倾向于前者,将可预见性限制于合同签订之时。美国法侧重于损失类型,要求违约方对所有预期盈利承担责任,不论其复杂程度或方式。法国法则更进一步,不仅考虑了损失的类型,还关注了损失的程度,即在多种盈利方式并存时,违约方需为所有可能的盈利承担赔偿责任。CISG第二十五条的规定则将可预见性作为一项豁免条件,对于可预见性的范围限定为:当事人明确一项义务的重要性,或从谈判中可得此项义务的重要性,除此之外可预见性都可以作用于违约方用以避免承担责任。CISG巧妙地将举证责任置于违约方,要求其证明自己对可预见性具有不可抗力。这一做法体现了无过错责任原则,即除非违约方能证明自己在订立合同时确实无法预见到损失,否则应承担赔偿责任。这种归责原则旨在保护守约方的权益,同时也考虑了公平与效率。
来源、转载:法律笔谈
凡本微信公众平台标明“转自”或“来源”的作品,版权归原作者及原平台所有,仅代表原作者个人观点,供读者学习、参考,不代表本所公众号观点。如涉及版权等问题,请在微信后台留言,我们将第一时间处理,非常感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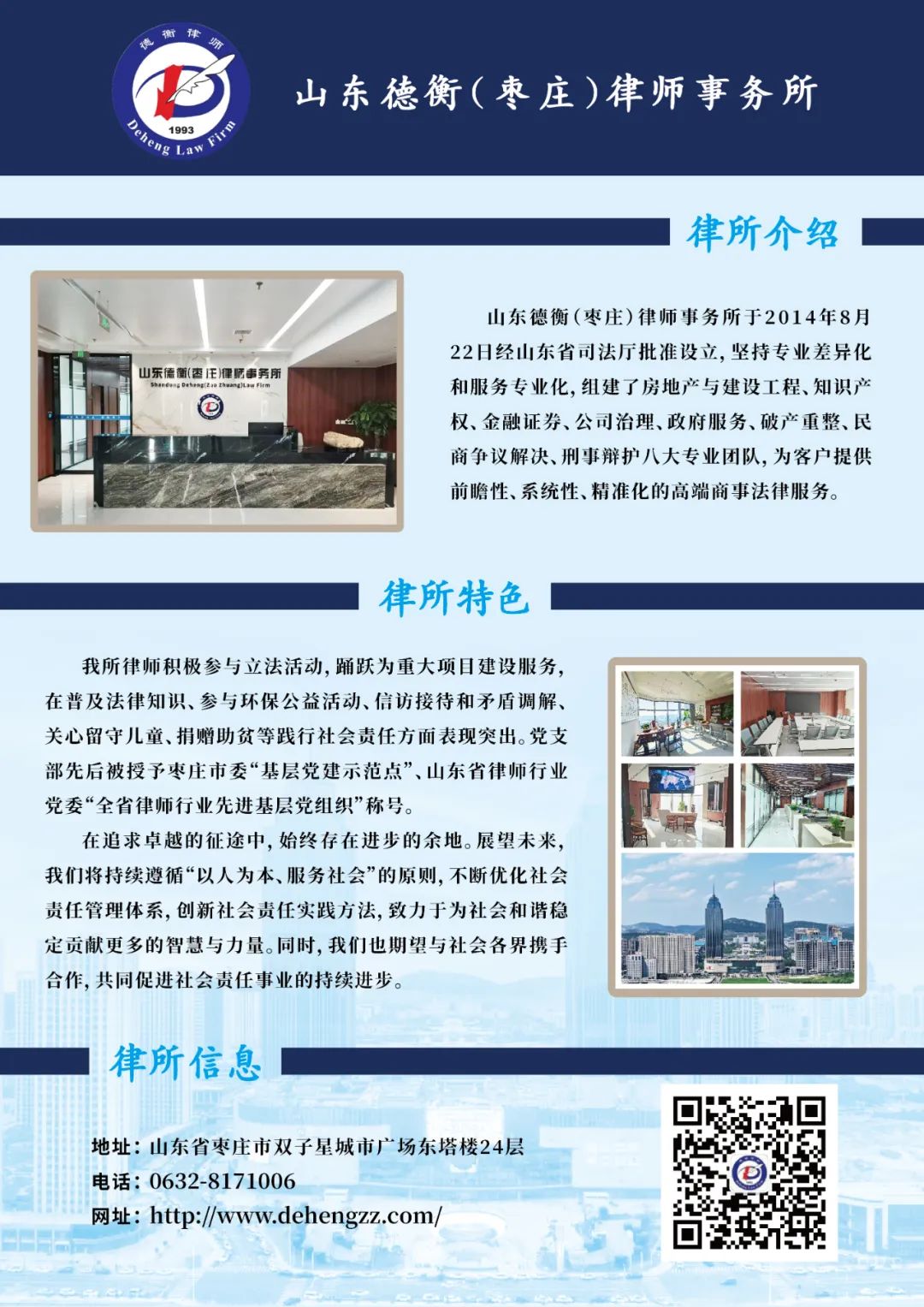
素材来源官方媒体/网络新闻
